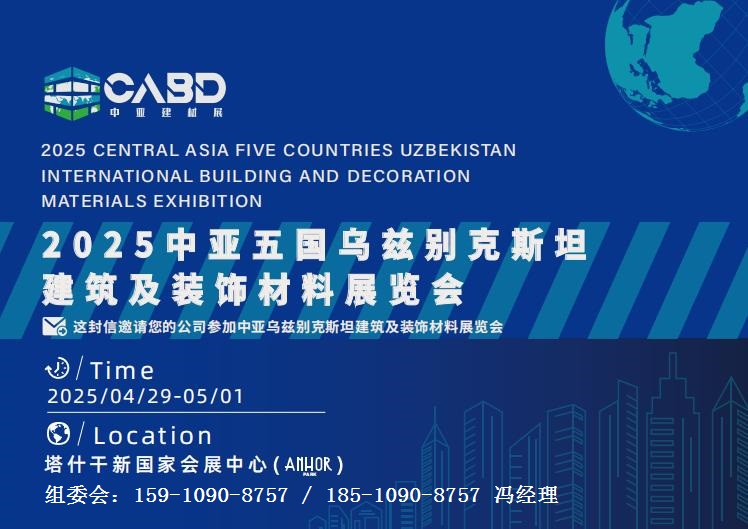大地有很多的儿女,牵牛花是其中的一群。
在农村的房前屋后、田间地头,在荒僻的路边沟旁,它几乎可以不受打扰自由自在地生长开放。它不挺拔,枝干柔弱弯曲,还长着茸毛,需要攀附在其他东西上,才能向四周蔓延,长成茂盛的一小片,仰起一个个小喇叭。或是红的,或是蓝的,或是紫的,或是白的。它不害羞,它不惧怕,它不躲避。即使有一株骄傲的玫瑰在它身旁怒放,它照样开心地抬起小小的笑脸。如果几头水牛觉得它味道不错,慢慢地把它嚼进肚里,它也不拒绝,知道命该如此。
狂风暴雨突然袭来,甚至下起冰雹,噼噼啪啪把它打得叶烂花落,它也不绝望,过几天又生出新叶,开出新花。它是真正的强者。它不需要肥沃的土壤,它不需要昂贵的温室,它不需要人们浇灌。春天一到,它不知从哪里钻出来,在你眼前爬着毫不起眼的小藤,不知不觉间,就仰起了一个个骄傲的小喇叭。它真正经得起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。它的种子,白色的叫白丑,黑色的叫黑丑。它们用于治疗水肿胀满、大小便不通、痰多喘咳、虫积腹痛有很好的疗效,还可以祛斑。
牵牛花几乎充盈着我的整个童年。那时的夏天,老屋前篱笆墙上,从春到秋,都长满了牵牛花。那些花婀娜多姿,随风摇曳,远远看上去,整面篱笆恰似一幅随风摆动的画。感觉只有篱笆上的牵牛花,才是最佳搭配。仿似“寻常一样窗前月,才有梅花便不同”,牵牛爬上了篱笆,立即就有了一番别样的乡村风情。
时下正是晚秋。十一月已经到来。十多天前还满树葱茏神气活现的刺槐,现已形销骨立只剩几枚叶片了,犹如举着降旗的残兵败将。就连一味疯长的野草也已乖乖缩回自己固有的领地,蔫了,黄了,枯萎了。惟独牵牛花不同。深紫的,浅蓝的,粉红的,条纹的,仍开得生机蓬勃顾盼生辉。有的“唰”一下子在荒草地绽开无数多情的笑靥,有的“忽”一下子蹿上枯枝擎起高傲的喇叭,有的在路旁沙地上绣出斑斓的图案。后来,我的目光久久停留在山坡中间由石块和青砖砌成的半堵残墙上面。墙上的爬山虎没了叶片,只剩几条细蔓紧紧攀附不动,如老人手背上的几根细筋。墙根的芒草也已无精打彩。却见四五朵红蓝两色的牵牛花在残墙上开得正艳,薄薄的花朵在清冷的秋阳下抖出妩媚的光彩。枯黄与娇艳,残缺与圆满,寂灭与生机,刚与柔,厚与薄,重与轻——世上难道还有比这更美妙更和谐的对比与反差吗?我一时忘了移步,默默凝视良久。
或许,你认为权倾一时是幸福,金榜题名是幸福,富甲一方是幸福,扬名海外是幸福。但对于我,最幸福的,莫过于夏日清晨从爬满牵牛花的山坡或木篱间走过。